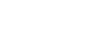幸福快乐修行的故事依依不舍
修行的故事
我始终觉得,言者有心。一个人时常把一些东西,用一种不容置疑的驳斥的态度,挂在嘴边上,那往往他心里对这些东西是有执念的。比如,有的人总说我已经忘了谁谁谁,实则最难忘便是谁谁谁。再比如,一个和尚天天说我不想吃肉,那他一定特别想吃肉,而且一定吃过肉。
2013年刚毕业工作那会,组织一帮驴友去参观一个邻省的旅游度假地产项目,浅识了老吴。在老中青三代混杂的几百号驴友里,老吴有一种不泯于众人的气质。他既不是那个驴友团的领队,也非一个盲从者。出发的大巴车开进我们单位院子的时候,他没有随着人群一拥而上,也不像几个自发的秩序维护者那样大声吆喝,试图将人群变得有序起来,只是一个人远离车辆和人群,也不躲到阴凉的地方,就在烈日下静静地待着。最后一言不发的上了我在的那辆车。
彼时车上只有一个导游座,而我和他都站着,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不坐,他也不坐。最后我说:师傅,我们挤挤?他才坐下来,坐了三分之一的屁股。我全身被汗淋透,坐到他旁边,转头看他,他却浑身出奇的干爽,额头都未沁出一滴汗,让我困惑异常。他头微微倾斜,盯着窗外看。
驴友这个群体有着热闹喧腾的属性,一路欢声笑语,车大约行进了两个小时,到了目的地,而期间老吴保持看窗外的姿势一动未动。中午的时候,活动的赞助方给驴友们发汉堡和饮用水,未出乎意料,老吴是最后一个来领的,从我手中接过饮食,他忽然右手自然下伸,指端下垂,手掌向着我,然后微微点头一言不发转身离开。
饭毕,驴友们在项目里自由活动,我同驴友团的几位领队躲在阴凉处抽烟闲聊。对面是一片湖,湖边有邻水的栈道,我远远的看过去,有一个模糊的身影盘坐在栈道上,炙热的阳光折射过来,那个身影却一点也没有晃动的痕迹。我问一个相熟的领队,这个五十来岁的领队,脸上流露出一种怪异的表情:那就是早上来的时候跟你一起坐的老吴。我疑惑的问:他这是?领队面无表情的说:修行。
而那时在我有限的理解里,所谓的修行,就是和尚与钵盂,道士和拂尘,还有一些所谓的看破红尘和遁入空门之类的呓语。我倒是突然对于老吴这种从未遇过的人有了一丝莫名的膜拜。
那次以后,又组织过几次类似的活动,老吴几乎每次都来,也几乎每次与我挤一张导游座。渐渐的熟悉,才发现老吴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到后来,他的话愈发的多了起来。他很少提及生活的种种,反倒是常讲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对生活对人生对自我的厌恶溢于言表。我问他修的是什么行?他说:摆脱繁杂的物质世界,远离纷纷的红尘,追求内心的宁静。
听得多了,我就认为这是一种矫情,世间何处不染红尘。
我加入了老吴所在的那个驴友团,同他们走了一次吴越古道,那次没有老吴,在江南第一池旁露营,周遭寂静,闻湖水涨落有微声,我突然有了老吴口中那种远离红尘的感触,但是第二天还是义无反顾下了山,回了南京。
2014年年初那会,驴友团的版贴里面有人发了一个帖子,几个驴友探访终南山,偶遇了几位终南山隐士,结草为庐,远离尘世,于山野中修行。所有人只把这个帖子当做一次普通的驴友行。老吴在群里仔细的问询,我们也未在意。
那年春节正月里,第一次参加驴友团的春会,我在热闹的人群里寻找老吴,始终不见他的身影,隐隐有种预感。而到了三月,驴友版里一个帖子被置顶:《寻找老吴》。发帖子的自称是老吴的妻女,说老吴在除夕夜留下一张纸几行字,字面意思大概是:我去修行了,我去追寻内心的宁静了,别找我。驴友们纷纷在下面留言,说猜测出主意。最后终于有人说:我去,老吴不会真跑到终南山当隐士去了吧。然后下面就不再有人回帖,只剩老吴的妻女一条一条的苦求。
后来半年,也有几波驴友去终南山徒步,都说没见过老吴。渐渐的,那个帖子也随着时间沉下去,无人再提及。
再见老吴已是今年驴友团的春会,我从老家回南京去的晚,到的时候众人已是酒酣,一层一层围在一张桌子边,我挤进去,发现人群正中坐着的正是老吴。他头发短的似刚出狱的犯人,一张脸上红黑相间,红的是像皲裂后新长出的皮肤,也像被酒熏的,原本四十岁出头的人缺有了五十来岁的模样。
所有人听他讲一个关于修行的故事。
这两年他的确隐居在终南山。
那年他看到那个关于终南山隐士的帖子,心动难耐,彻夜未眠,心里有一股执念:这才是我想要的修行。他在上搜终南山,搜到一本叫《空谷幽兰》的书,作者是一位美国人,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关于终南山隐士的故事。老吴神往不已,终于在那年除夕夜,抛弃妻女,留下只言片语,一意孤行的上了西去的火车。
在西安下车,坐汽车过了长安县,往南不到五十几里,就是悠悠见南山的终南山了。大年初二这天,老吴把证件、钱包故意遗落在山下一个镇子的旅店里,背着一点干粮和两件衣服就上了堆满雪的终南山,自此消失于人间两年。
终南山是千里秦岭的一处支脉,古称太乙山,就是太乙真人的太乙,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自古就有士大夫、文人、佛道修士隐居在这里,最早的隐士据传有商周的姜子牙,后来还有医圣孙思邈,纯阳真人吕洞宾等。
老吴看的那本美国人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是第一本描绘当代终南山隐士的书籍,它叙述了终南山隐士们的隐居生活,他们大多信奉佛道,安贫乐道地远离现代城市,在山中与清风为伍,与绿野作伴,摒弃了物质的享受,追求内心世界的富足。
老吴从山下的小镇出发,去山里寻隐士问道,在离山最后的一个村子,他遇见一个蹲在自家门口吃面的老农,他问: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隐士?
老农头也不抬,大声的提溜着宽面:你找和尚还是道士?
老吴说:找真正的智者,能让我解脱。
老农一口浓痰吐在门口被扫成一堆的积雪上,自然地伸出手。
老吴皱了皱眉,内心感慨,即便是在这钟灵毓秀的终南山脚,也脱了不了那层俗气,于是更加坚定,把身上唯一的递给了老农。老农咧开一嘴黄牙,遥指不远处几座巍巍的山:神经病多的是,你随便找找就找到了。
老吴郁结,还是往老农指的方向头也不回的去了。
上山的路比想象的要好一点,似乎是千万人走过,在荒山野岭中硬生生走出了一条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太阳跳出山涧,阳光打在白雪上,折射出异样明亮的光芒,老吴心安,不再往回头看。到了一处山谷,城市这个时点的车水马龙的喧嚣,在这个山谷里没有一点痕迹,只是山林里传来不知什么动物的轻啸,悠远空灵。
眼前是几座茅蓬,老吴走进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座茅蓬,与周边几处的破败相较,显得有些堂皇。与其说是茅蓬,不如说是山居别墅,水泥切成的三间屋子,只是在外面又打了一层白石灰,屋顶铺了几层茅草,石头堆叠成半人高的院子,像是一个剃了时下最时尚发型的现代人,倒是穿了一件道袍那样,说不出来的别扭。
老吴轻轻的唤了两声:有人吗?
一个中年模样的男人从最中间的屋子里走出来,疑惑的看着他:大过年的怎么跑山上来了?
老吴说:我来修行。
中年男人掐了一个道指,点头示意。然后请老吴喝了一杯山茶,山茶味极苦,老吴问:我该如何修行?。中年男人刚想说话,唐装上衣口袋里突然传来震动和铃声,男子自然地拿出,接起了。老吴蹙起眉头,沉默不语。
接罢,中年男子语调清寡的说:吾辈来此,只求摆脱物质的享受,独自面对孤苦,寻得内心的安宁平静。说话间,一个农民模样的妇人推开石头院子的木门走进,朝中年男子微微弯腰点头:师傅,你要的素馅饺子我给你送来了。中年男子转身进了屋子,老吴看见他递了一张红色的钞票给妇人,更沉默起来。
中年男人请老吴吃了顿素馅饺子,老吴吃着吃着,反倒吃出了肉的味道,顿觉倒胃口,没吃完便辞别,往山的更高处走。
又走了三个小时,到了云深处,雪和云朵便混在了一起,老吴寻到了一处山洞,山洞里住了两位比丘尼,看起来在山上居住的时日不久了,灰色僧衣已褪色几近素白,阴冷的洞中只有一些粗陋的锅碗瓢盆,也大多有裂纹缺口,洞口一片菜地上只看到种子裸在外面,并未发芽。年长的老尼双手合十轻点了下头,便不再瞧他。年纪较小的比丘尼与他攀谈,谈及老尼,说她修的是闭口禅,已经多年未开口了。
老吴顿生崇敬之情,双手合十朝老尼鞠了一躬。他转身问年轻的比丘尼:女师傅,我该如何修行?那位女师傅也不说话,示意他跟着,便往洞旁走。老吴便跟着她,在雪地里拣干燥的柴枝,用破烂的麻绳捆好,背回山洞。接着,用火柴点燃一捧枯树叶引火,慢慢的添柴,一个自制的木架子上挂着一个瓦罐,煮了许久后,终于有一点淡淡的粥香。年轻的比丘尼从一个布包里取出三个干裂的馒头,一个递给老尼,一个递给老吴,一个咬在自己的嘴口。
食不语。可老吴觉得那是他吃过最香甜的米粥和馒头。接着半个下午,老尼和年轻的比丘尼盘坐着,不发一语。老吴坐了许久,终究还是坐不住了,站起来双腿麻木,打了个踉跄。年轻的比丘尼指指快落山的太阳,对老吴说:你若受的了这清苦,便再往上去,那里有几位大师苦修的山洞,若受不了,下山去。
老吴觉得这本是自己追求的东西,哪有什么受得了受不了的,便径直又往山上去了。又行了半个小时,一个黑洞洞的山洞,他朝洞口窥探进去,不见人影,壮着胆子往里又走了几步,隐隐似乎听见淡淡的声音,像是呼吸声,他借着洞口的照进来的微光,才发现一位眉发曳地的老人枯坐在洞里,他道了一声阿弥陀佛,半响,洞里才有另一声暗沉晦涩的阿弥陀佛响起。
他跪在地上:求大师留我在此修行。
老僧幽幽冒出一句:你留或修行,在你,不在求我。
老吴自此留下。洞中无青灯,心中有古佛。时常有山下供养的乡民还有远来的旅人给他们送一些干粮。最开始的时候,老吴学着老僧就着雪化的水,吃些干粮,起初闹了几次肚子,甚至发烧,就硬是撑过去,但他觉得这就是修行。
山中的日子很是清苦寂寥,但是大概是应了那句禅语:山中一甲子,世上已千年。很快大半年便过去,老吴的头发也垂到肩头。这期间倒是发生了几件趣事,老吴百无聊赖之时探寻了几处人去洞空的处所,勉强找齐了一套锅碗瓢盆和其他简单的工具,便有一天生起火来,煮了半锅清汤馒头,放进一把山间的野蕨菜,他盛了半碗递给老僧,老僧呼啦啦的吃完,明晃晃的篝火多年后第一次照亮阴湿的山洞,馒头屑沾染在老僧花白的长须上,老吴看着笑了,老僧也笑了。
老僧问他:你是有家的人吧?
老吴沉默许久,反问回去:您呢?
老僧老神在在的闭眼,脸上没有一丝烟火:尘缘已断。
老吴问:怎么才能心如止水?
老僧:修行到了,自然忘了。
那夜,老吴偷偷的把收在衣服里的一张照片放在快燃尽的篝火里烧了。
手中的照片烧了,心中的尘缘烧了吗?
在山上的日子是孤寂的,除了吃饭睡觉,便是枯坐,渐渐地,老吴也能如老僧一样,不必躺下才能入眠,坐着坐着就是一夜。没有繁华喧闹,没有灯红酒绿,老吴觉得找到那片寻找已久的宁静。
他问老僧:我找到了宁静,然后呢?
老僧说:一直保持宁静。
老吴却开始困惑。
这种静默的日子有一天终于被打破。
那几天山里来了好几拨人。先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妙龄女孩,寻到洞口来,见到蹲在洞口吃水煮馒头的老吴,便拿出一张照片问老吴有没有见过照片中的人,老吴隐隐有觉,但是还是说:好像没见过。洞中却突然传来瓷碗落地破裂的声响。女孩疯似的冲进洞中,老吴楞了一会跟进去的时候,却看到女孩泪眼已婆也就是说娑,老僧闭着眼,洞中的篝火渐渐燃尽。
女孩开始撕心裂肺的嚎啕起来:大,大,我是碎娃子啊,我是.......
老吴慢慢走远,而洞里传来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尔后又越来越小起来。老吴去不远处的一处峭壁边上坐着,云层从身上飘过,他伸手去怀里想出掏点什么,最后还是无力的往东南方看去,却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眼。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老吴回到山洞,已是静悄悄的。他没有生火,老僧没有说话,一夜如是。
又过了几天,两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也出现在山洞里。老吴还是默默走开,再回来的时候,那些锅碗瓢盆碎了一地,每一片上都能嗅到点味道,有愤怒,有怨气,还有些浓稠的想念与不舍。那一晚,老僧念了一夜的《金刚经》。
又是一年冬,终南山被雪掩埋,人烟更寂静。除夕那天,山民送了一些木耳、蘑菇,老吴泡了许久,准备晚上煮一锅水煮馒头。他要出去找柴的时候,老僧说:我去吧。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山里的雪却把山野照的透亮,老僧还未回来。老吴隐隐不安,出门去找。在那处峭壁的边上,找到了老僧,他仰面躺着,丝丝缕缕的热气升腾在嘴边,正在呻吟,雪地里一片殷红。老吴冲过去,抱起他的头,热乎乎的,一块尖尖的石块上还有余温。
老僧断断的喘着粗气,嘴唇不断颤动,老吴低头把耳朵凑过去。
碎娃子,家,碎娃子,家,碎娃子........
老吴抬头,这天没有云,从峭壁看下去,似乎能看到山下的点点灯火,还有微微的爆竹声穿越了天际,划破了几千年的宁静。
老吴背着老僧下了山,下山的路同上山的路一样长,却走的异常轻快。
山下村子的卫生室,二年没见过灯光的老吴有些迷眼。喝了一斤酒的村医生闻讯赶过来,边帮老僧包扎边愤愤的用秦腔骂道:隐怂的居,修球的行,婆姨不要了,娃不要了,还是人吗?
那个五十岁的开外陕西大汉越骂越狠了,老吴却从老僧紧闭的眼角边看到一股浊流顺着厚重的鱼尾纹流下。
老吴把老僧留在了山下,独自回了山。他在想:老僧会回来吗?
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山洞里始终一个人。
时常供养他们的山民上山送吃的,看到了魔怔的老吴,他呆呆的盘坐在那处峭壁旁,对他说话,他不语,摇动他的身子,他任摆布,把馒头撕碎了往他的嘴里塞,卡在唇齿间。比丘们来了,齐念阿弥陀佛,道士们来了,齐念无量寿尊,万千神佛却招不回老吴的魂。最后一个每年来山上短修的居士,叹了一口气,凑到老吴的耳边低声说了句:走,回家。
老吴像是突然回了魂,嘴里喃喃道:回家,回家,回家.....
这一年驴友团的春会,大伙就着老吴的故事喝光了所有的酒,末了老吴的老婆开车来接她,三十大几的女人脸上却有像五十岁的沟壑。老吴踉跄的跑过去高兴地埋怨道:叫你先去接闺女的呢?
很多人起哄:老吴,你还回终南山吗?
老吴头也不回。
回球的回。
受风寒浑身关节酸痛手足麻木中草药嘉峪关白癜风治疗费用
-
狗狗挤肛门腺的方法位置
菜谱2022年06月17日

-
狗狗挠眼睛的问题位置
菜谱2022年06月17日

-
狗狗得了青光眼怎么医治位置
菜谱2022年06月17日

-
狗狗得了青光眼怎么办图位置
菜谱2022年06月17日

-
狗狗得了血管瘤怎么办图位置
菜谱2022年0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