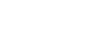一九八七年搭配
一九八七年,秋。
还是晨早。行人,桐城的街道空寂无声。路灯尽头是一片黯淡的灰。她在黑暗中行走,努力搜寻图景。行李箱在身后发出沉闷的声响,在寂静的秋日清晨显得格外突兀。
忽然一股浓重的悲伤向他袭来。一别经年,行迹匆匆里她已记不起他的脸。怎么记都记不起来。一切都变换了模样。她感觉的脚步在寒风中凝固了。而记忆的那一头,他早已将她忘记。他不曾记住任何人,也许是假装遗忘。
她将脸埋进双手。冷寂的秋日清晨,这是独属于她的。就像最后那晚,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失声痛哭,却没有任何人听到。
那年桐城的夏天雨水异常丰沛,记忆中是一片葱郁的绿。仿佛还在昨天,她独自来到这座空寂的城。在一家小小的咖啡馆中流连,在最里面的座位看窗外人来车往。她迷恋这样清淡的时刻,于缓状态有所下滑。在2010年邓华德出任中国队主帅之后慢的车流中看傍晚的归雁。有时她会拿起相机拍下窗外的风景。孤寂的身影。一片落下的桐叶。荒凉的街道。抱着婴孩的年轻女人。隔着玻璃门,它们看上去清寂而朦胧。
当她再度拿起相机的瞬间,她不会想到一个星期后她将与照片中的某个男人相遇。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喝黑色的咖啡。他有着最黯淡的眼神,也许他的眼睛里盛满了墨汁。
你叫。
合欢。
他用指尖拨弄着桐叶。从树下走过时,那片叶子刚好落下来。他伸手去接,像是接住雨天的水滴。我没有名字,也许有过的,但我忘记了。
夏天刚刚来临,置身在午后的日光中眼前一阵眩晕,她将手指抵在前额上。他向树荫深处走去,不再看她。忽然她停下脚步,我将名字分你一半吧,你叫合,我叫欢。
他大笑,沉郁的笑声像金属丝,冷硬的,闪烁着寒光。多年以后,当合欢在那座名为 云开 的咖啡馆深处听到相似的笑声时,眼泪落下来。
她和他相识是在八月。夏天快过去,秋天却迟迟不肯到来。正午的日光被门前几株香樟切断。咖啡馆中一片寂静,空气里流淌着Carpenters忧伤的歌声。她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看他从窗外走过。一直以来她都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癖好,喜欢盯着别人看,就像观看一场电影,从序幕到剧终。
后来他们谈天时,她忆起了学生时代由于不喜欢抬头看黑板,被老师喊起来站到教室最后,面壁。她没有哭,也没有觉得屈辱。剩下的半节课在朦胧的睡意中度过,她甚至在睡梦中梦到了自己坐在荷花池边,下面是接天的莲叶。她想,就是从那时起,她习惯了盯着别人看,尽管她的眼睛什么也没装下。
他走进来,融入咖啡馆黯淡的光线中。大概是觉察到她的目光,他径直朝她走去,在她对面坐下。,认识么?
她摇头。于是出现了开始的一幕。他询问她的名字。她感觉指尖冰凉。咖啡馆老板、服务生是同一个人。她看着他,暗自忖度,也许他们三有着相似的年龄。到外面走走吧,她提议。走出店门的刹那,日光照进眼底,像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屋子。她忽然感到一阵悲伤。深沉的,如丝线般缠绕,她感觉难以呼吸。
你叫合,我叫欢。
第一次相见,她将名字分给了他一半。第二次相见,他已不能将她认出。同样的地点,指针划过了几道圈儿;同样的人,表情却是未曾相识。她没有走过去跟他打招呼,眩白的光影下她隐身在黯淡的角落,一边喝着冷涩咖啡,一边静静盯着他看。
直至人潮散尽,馆内又重现那个下午的光景。他,那个封存于相机中的男人。咖啡馆老板。还有她。阴柔的夜色中甚至还播放着和那天下午一样的歌。YesterdayOnceMore。她盯着他看,一直盯着。她不愿相信她被他遗忘了。就像多年以后,一九八七年的那次寻找,以及,寻找过后的更多年以后。
抬头时他发现她直逼而来的充满仇恨的眼神。他顿时感觉如坐针毡,握着杯子的手在瞬间灼烧起来。她依然盯着他看,这让他觉得有必要跟她说两句话,尽管他也就间谍罪名接受审讯。由于他的辩护律师团退庭抗议不明白为什么。同第一次一样,他在她的对面坐下,一模一样的对白和音节顿挫:我们,认识么?
是的,我们好像是见过的。她笑,忘记了悲伤与快乐,忘记了和站在不远处对着她看的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他一面研磨咖啡豆,一面注视着这里。她置身在两个男目光下,她只知道其一。
盯着对方的细长手指,她忽然发问道,你叫什么,我叫合欢。
然后空气凝固下来。
一个星期后,她离开了那家咖啡馆,一个有着深褐色胡须的男人。她和他不熟,他以为他和她很熟。多年后当她起那家咖啡馆时,她只记得窗外的香樟和喧嚣的车流,一个黯淡的男人,一个固定的座位,一杯温热的咖啡。而他,那个咖啡馆老板,也和他一样。他们都忘了她曾来过,都忘了他们曾置身在一段安静的里彼此对望,听着Carpenters的忧伤的歌声。
从一家咖啡馆走进另一家咖啡馆,从一叠相片走进另一叠相片。两堆相片中出现了一个相似的面孔。她在灯光下反复观摩,最终认定就是他,一个她为之命名为 合 的男人。她隐约记起之前和他见过两次。他们都没想到,竟会在另一家咖啡馆重又遇见对方。
这是他常来的地方,几乎每个午后他都在这里度过。在寂静的光河里看书,抄写。尽管已经告别学生时代多年,却一直保持着抄写的习惯。他抄波德莱尔,他抄里尔克:
我极其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切,突然想到,这是我命定的要来的地方。因为现在我相信,我终于抵达了中的那个 点 ,那将是归宿。的确,命运来临的方式奇妙莫测。
我爱过的那些灵魂,我歌唱过的那些灵魂,请给我力量,支持我,让人世的虚妄和堕落的忧郁全都远离我。
直到有一天,他的双腿带他去到另一家咖啡馆。每天下午他都会从那里经过,却从未走进去。 不喜欢过于华丽的装束。 当合欢问他为什么时,他这样回答。他只是无意识地走进去。头痛。想要走过一段长长的路,借以缓释双眼的疲惫。在那里他遇见了她,和她谈天、说地,撕碎落到掌心的桐叶,趁对方不注意时扔到台阶的护栏之外。碎片下落时他感觉到左脸开始升温。
那是一个愉快的午后。多年后回忆起来,他和合欢都这样认为,是一本华美的画册,刹那、那个瞬间,一一完美印刻。但他却不曾记住她。几天后他又来到同一家咖啡馆,而后去了另一座城市。他总觉得累,也许数十小时的车程和窗外的美景能够安慰他。短暂的停留后,归来。两个星期后他在这里遇见了她。
我们,认识么?合欢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在桌椅的尽头看见她,左手托着半瓶香槟,凌乱的发丝散到唇边。她看上去总是浪荡不羁,似一枝妖冶的玫瑰。有时却温润如玉。是两个人么,他笑。挨着桌子坐下,她对他摆摆手算是招呼。空气中是忧伤的Carpenters的歌声。灯光暗下来,他忽然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还要喝的么?没等她回答,就起身到柜台旁的箱子里取了两听青啤。他喜欢听装,有金属的质感;合欢喜欢瓶子, 用力摇一摇,能看到酒花飞舞 。
会在每个下午遇见对方。准确说来,自从合欢来到这家咖啡馆后,他总能从玻璃门中看到她。悄声走过,在她对面装作不经意地坐下,就像第一次那样。有时合欢扭过头去,他顺着她脸的方向看到他俩在镜中的合影。她在笑,于是他看到镜中的自己微微动了下嘴唇。
渐渐地,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熟络起来。她拍些照片,精致的,在背面写上几行字以示纪念。遇到他之后,合欢就把书写任务扔给他了。 你写得比我好。 他笑笑,接过两包重重包裹的相片。体积不大,却挺重。拆开牛皮封纸后,同合欢一样,他一张一张浏览过去。都是些灰色调的,或者极其明亮的色块。他无法想象一个人竟然在两种迥然相异的风格间游刃有余。就像她,有时明媚有时黯淡。而后,在那叠图画中他遇见了自己。两次。一次是蓝色暗纹衬衫,黑色领带在风中扬起。另一次也是这样。拍摄的时间、地点不同,却像是在同一天。一样的风吹的角度。
他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他无法像个局外人般欣赏相片中的自己。傍晚时合欢出去散步,她要他陪自己去。他摇手说想把这些写完。淡黄色的光铺满咖啡馆的地面,每一寸桌椅和墙壁。那些相片上也落满了黄昏的颜色。犹豫良久,他偷偷将它们抽离,夹到那本薄薄的里尔克的诗集中。
他们会一起出去玩。她习惯性地将他看作,虽然她和他可能有着相同的年龄。他从不提及他的过去,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合欢只知道他喜欢看书,并写下长长的。他的字迹清秀,冷硬的,像他金属般的声音。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九八七年,秋。凉薄的雾气里再找不到那年的咖啡馆,它消失了。道路也变换了容貌,它们成了宽阔平坦的繁华街道。她忽然感觉到一股浓重的悲伤。像是被这座城市吐出来,孤零零地遗落在外。
秋意寒凉。合欢在一家服饰店挑了一件毛衣。很明亮的颜色,忍不住联想到向日葵。也曾想过在满园的金色花朵中沉沉睡去,像漫画中描摹的那样。回来时路过卖花草的小铺,玻璃杯中插着几枝妖艳的玫瑰。还有紫色的,说不出名字的纤长的花枝,上面沾着几滴露水。也许是雨水。水滴。合欢从那些花草前缓慢走过,却没有找到喜欢的。花盆是俗气的纯色,有些种在茶杯里。花是单调的绿。她在摊位前站定,想起上次在花草市场。精致的花盆,行将枯萎的花;翠色的花,古旧的花盆,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要是交换下就好了。
可以啊。 一旁的男生说。从合欢停下脚步抚弄那些花时,他就一直打量着她。他走过来移出那两只花盆,将剩下的排列整齐。一个近似六边形的轮廓。这就是店主了。合欢把手伸进衣袋,她感觉手脚冰凉。犹豫了片刻,看他给它们修剪花枝,而后离开。就像这次,蓦然转身。空寂的楼梯上她想,下次见面一定要带给他一盆最美的花。
不对,两盆好了。和他逛街时一起买。
只是,还会有下次么。
为什么离开。合欢自己也不知道。说走就走。不留下任何讯息。不留下一个字。当坐上开往南方的火车时,她沉默着闭上双眼。不见不念。此生不念。然后,眼泪落下来。她知道舍不得,却没有办法留下。她想要离开,飞速逃离。
如若,如若他能精细到捕捉她的每句话中的每一个音节,也许她的离开就不会显得那样突兀。像干净的画纸上忽然滚落下了磨块。
合,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
不会的。他在拨弄那盆吊兰,连续几天的阴雨,叶尖已开始泛起枯萎的黄。他不会注意到那句话,不会去忖度那话背后汹涌的浪潮。不过是句玩笑。他的一声 不会的 也只是悬浮在空气中的轻声应和。他甚至没听清对方唇齿间流淌出的音节。在他的世界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漫不经心,一切都只是水中的浮花。
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
一个人行走时,合欢常常想起这三个短句。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唇齿间挤出来。像是走过狭长的桥,每一步都是那样生硬而小心翼翼。很多年后,这句话似乎占满了他和她的所有回忆。而他,却从未睁开眼睛看过这句话。他不会记起来,就像他的名字。人们喊他 秋生 ,她把她的名字分他一半,他却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名字。
他带她出去玩。她习惯视他为父亲,有时是大哥哥。他不提及他的过去,她不提及她的过去。对于桐城,她是个异乡人。他不会问她为何来到这里,也不会关心是否有一天她会突然离去。
我一无所有。 一天他对合欢说。
不,你有名字,你叫合。她还想说,他有她。觉得矫情抑或是自作多情,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在桐城之前,合欢曾无数次幻想着一个人徘徊在午夜的街道。有着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长长的的路和迟迟不肯到来的白天。而现在,当她来到梦中的幻景之城时,她犹豫了。一个人在这里你会害怕么。
合欢抬头,朝他看了一眼,而后目光向四周扫去。两条寂静的街道平行着伸向远方,中间被花坪隔开。夏天快过去了,桐叶开始一片片落下来。长椅下稀落地掉了一片两片。合欢踩上去,脚下传来干枯的断裂声。 能确保我是安全的,就不怕。
我不怕夜的黑,我怕危险。她的声音清脆,他在黑暗中笑。
她想起一次,雨天,他没有和她一起坐车回去。因为什么,她忘记了。七点多时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她不知道是哪辆车。那时还没有,只得在暗夜中等待远方亮起的车灯,红色的,闪闪烁烁。在风中站了半小时后,她走向站牌,才发现已经错过了末班车。那一刻,她似乎听到自己潮湿的叹息落到晚空中。
还要两个小时。两小时后才会有91路车。她拦截了一辆公交,在清冷的声带下司机对她说道。是一种满怀敌意的声音。多年后,当合欢独自行走在陌生街道时,常能想起这一晚的漫长的夜和司机的冰冷语调。她在风中来回走动。平时有他在,她不觉得害怕,甚至希望时间流逝得慢些。是那样享受和他一起的时光,而他向往着远方。与她的闲聊也许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好方式。
在风中不停走动,就不会有人发现她在等车。她不愿别人知道自己在等车。寂静的街道让她觉得危险。只要他不在,只要独自一人,在这漆黑的夜,她就觉得会有一阵漩涡将自己吸进去。
对合欢来说,桐城始终是一座陌生的城。仿佛玻璃窗上蒙上一层薄雾,看不真切。无论八七年之前,还是之后的N多年。每当穿行在迷宫般的巷子里,都感觉像是行走在棋盘上,怎么都触摸不到尽头,怎么都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而她却总试图能够摸索出一条路,清晰的路,在高空俯瞰全局。
那个夏天,发生了什么呢;这个秋天,她又期待着能发生什么呢。旧时的咖啡馆、街道、东瀛广场,还有每个夜晚都会爆满的马戏团早已改迁。纵是繁华一片,却是满目荒凉。人不在了,人又回来了。那个人还是没出现。还有个人早已被她弃掷在那晚的歌声里。
你叫合,我叫欢。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这城里还能找寻到他的行迹么,只怕早在风中行销迹散。而她,又要如何才能在茫茫海中将他打捞出来。最后的最后,在最初的桐叶的飘零里,她望见了:时光成海。
不过是一转身。
揭阳白癜风治疗费用宿迁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
小孩子消化不良的症状
- 上一篇:主人家有一棵苹果树搭配
- 下一篇:再度指责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低下搭配

-
清洗仓鼠用具注意哪些问题位置
凉菜2022年06月13日

-
深红玫瑰鹦鹉饲养养深红玫瑰鹦鹉的细节位置
凉菜2022年06月13日

-
使用强迫的方法来训练银狐犬可行吗位置
凉菜2022年06月13日

-
你的哈士奇会握手吗位置
凉菜2022年06月13日

-
你正在犯饲养泰迪犬的哪些错误位置
凉菜2022年06月13日

-
你知道为什么拉布拉多犬一定不可以喝牛奶吗位置
凉菜2022年0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