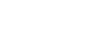根除愤怒的种子
我们有一种普遍的错觉,就是认为那些令人生气、发火的事情存在于外界,与我们自己无关;这些事情让我们得不到安全和保护,并威胁着我们的舒适或地位,因此有必要去保护容易受到伤害的自己。但实际上,愤怒会削弱我们,使我们变得狭隘。如果有勇气正视愤怒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就能培养出开放的心灵——具有真正慈悲的心灵。
我本人在应对愤怒时曾去学了几种武术。我学习武术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御外在的敌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令我愤怒的原因。一段时间里,我热衷于居合道(译者注:日本剑道的一种流派),也就是练习使用武士刀的功夫,譬如拔刀、挥砍、收刀入鞘等。大致说明一下,居合道这个词的意思是:和谐地适应任何环境。与许多其他武术不同,居合道并不是用来跟人打斗的,其实这才是它的关键所在:为了创造一种与自我和谐相处的关系,我们必须面对内在的敌人——自我的愤怒。
我时常留意到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体验着愤怒。与此同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更普遍的愤怒感;也就是说,愤怒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例如我们所认为的幽默有时非常不厚道,很多我们认为好玩的事情,其实都与捉弄他人有关。比如有些滑稽剧里面,人们跑来跑去做的都是一些刻薄的、居心不良的事情,以图找些乐子。不管在电视节目、还是新发布的病态网络视频里,我们发现幽默这个词就代表着嘲弄他人、令他人沮丧,或是羞辱别人,让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别人受到某种屈辱。我们可能要问问自己:“这好笑吗?”不好笑!嘲笑别人的不幸只不过是我们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我们是不是曾经对他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你这人真懒!”“你是个坏蛋!”或者“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混蛋!”当然,我们都干过!不过以这种或那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而已。或许,我们会说:“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不干了!”或者“都是因为你,我才遭这罪!”好像我们相信:通过贬低他人或把自己不幸的矛头和责任推给他人,就可以使自己好过一点,或是可以缓解自己的缺失感。但愤怒并不能使感觉变好。如同邱阳创巴仁波切所说:“攻击他人并不能真正消除痛苦!你越攻击,就越增强了攻击的能力,它会不断创造新的东西让你去攻击。直到最后,攻击性发展到充斥内心的所有空间,在所有环境里都根深蒂固。”
巴利语“dosa”指所谓的“三毒”之一——“嗔”。而“三毒”——贪、嗔、痴,一直束缚和控制着我们,压制我们的善心并迫使我们去伤害他人,甚至可能对最关心的人造成最大的伤害。其实我们不想伤害他们,也不想伤害自己,但被自己的嗔恨所驱使不得不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产生的某种感觉其实是更深层次的情绪或经验的外在显现。
要探究这是否可能,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的愤怒到底来自何处?愤怒的另一面是什么?答案是:恐惧!在超越内心的愤怒和恐惧之前,我们无法获得内心的自在。是什么导致恐惧?从根本上说,是对“无”、对死亡的恐惧,担心失去自我和被遗忘。但是对“死”的恐惧却会转变为对“活”的恐惧,因为无常本身正是生命的基本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恐惧中包含了愤怒的种子。
如何打破愤怒的循环呢?我们通常都是通过自身的体验来了解愤怒,但如果在生气时被要求停下来,并去思考“愤怒是什么”时,却很难看清它到底是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带着觉知、带着正念去接近内心的愤怒,这种观察就变成了有效修行的一部分。最终,我们发现可以从愤怒那里学到一些事情。
愤怒就是一行禅师所说的“习气的力量”。如同大多数习气一样,只需要遇到某个特别场景,或某句话,或某突发性事件,弹指之间它便会发作。即使我们有过类似开悟的体验并瞥见我们的自性,或有那么一两秒体验到某种极其喜悦的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分钟或一小时后习气不会重现。如果有人做了一些事情令你发怒,可以问一下自己:“是谁被激怒了?是谁在愤怒?”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一个“我”在生气,也没有一个“我”需要去保护。
然而,可能会有些事让我们的怒火一次又一次地被点燃,准时得像个闹钟。也许我们知道那些事情是什么,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通常其他人也会告知是什么让我们的怒火爆发。但这些习气触发点正好提供了更深入看清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带着更全面的理解和更多的慈悲心,去看待那些激起愤怒的事情,并密切注意着内心的变化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的间隙专注地向内观照。
那么如何找到这个间隙,让我们从愤怒中脱离出来?许多佛法道理教导我们万法并非坚固不坏。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就会发现愤怒和憎恨的基础正被逐渐破坏并最终毁灭,这就是佛法里所谓的“三法印”之一——诸行无常。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也体现了事物转瞬即逝的本质。有些事情让我们生气,也许是一天的开始时刻就在家中和伴侣争执;几小时后,在工作中仍然对此事念念不忘;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午餐时继续惦记着;直到回家,我们仍抱着这事不放。但是它在哪里?这个事件在哪里?就像昨晚的晚餐——它早就消失了!
一次又一次,我告诉学生如何应对愤怒:“这种练习其实就是保持警惕!”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练习,因为它违背了许多我们原本认为神圣的观点。我们很多人都膜拜一些特殊的“神”,不是上帝、耶稣或佛陀,而是快乐、舒适和安全等等。尽管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但仍旧紧紧抓住那些我们认为会带来安全的东西。我们坚持认为它们能消除各种不适,而当它们从我们的掌握中溜走时,恐惧和愤怒就出现了。
正念修行中的一部分是去观照我们的反应和认知。如果我们大家真的是一体的,为什么要切断与伙伴、同事或朋友的联系?如果我的手很痛,就应该砍掉它吗?当然不行!我会悉心照顾它,会用点泰诺止痛。然后再仔细地去观察是什么导致疼痛——可能是受伤了,也可能是患上了关节炎,需要考虑采用一些治疗方法。但当愤怒来临时,我们却会封闭自己,因为我们平时努力营造了一个自己,此时就必须来保护这个自己。愤怒限制了我们全面审视自我的过程。愤怒有很强的分裂力量,它阻碍我们过一种与他人紧密联系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在愤怒中,我们无法体验浑然一体的整体感;反过来,愤怒将我们孤立起来,加强自我分裂的情绪,并阻碍我们认同他人、同情他人。
正念要通过禅修来培养。令人吃惊的是有很多东西在参禅中渐渐浮上表面。在开始禅修的前几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随和温厚、容易相处的人。但是在密集禅修期间,我简直不敢相信心里会出现这么多气愤、乃至暴怒,我居然准备杀死老师、杀死和尚、并烧掉寺庙!它和我认为的自己形成鲜明的对立。我的愤怒日益严重,特别是当我分配到用牙刷洗马桶的任务之后。但从始至终,我一直坚持禅修。而且在某些时候,用牙刷刷洗马桶也变成了一项保持正念的修行。
佛法处理愤怒的方法和心理治疗有一点不同,佛法不会告诉你去摔打枕头、打开窗户高声尖叫。当我还是一名心理医生的时候,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丑模样的充气不倒翁,你打它的时候它只是弹回来而已。我会告诉病人说:“狠狠打,直到把它彻底打倒!”但佛教的方法不是那样。在佛教中,我们努力地去探明我们原本的真实自性。当你生气时,你的愤怒其实在指向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其实就是潜意识里我们对自我的各种信念,通过它可以揭示我们创造的自我认同感。
勃起功能障碍是什么原因
MACC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