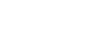江南吃相凶猛小说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欢喜的压抑不住的笑就被一场意外的事故压塌了。这件事如凶恶的老虎,毫不留情地扑上来就咬,把我脸上和内心的笑都撕扯得稀烂。展现给我的那种零乱的红色,让我眼睛都失去了滚动的力气。
母亲在小石灰窑打工的时候,不慎被滚落下来的石头砸烂了脚。斜躺在椅子上的母亲尖尖地叫着“痛、痛。”她脚上的血已经暗得发灰了,淡黄色的解放胶鞋和那些暗红色的血块都凝在一起。我十分害怕地伸过手去,象去摸一堆让人看着就恶心的毛毛虫似的。刚碰到鞋,母亲就厉厉地叫起来,那如剑一般的喊声仿佛不是母亲在叫,而是我的心被刀在一点点割。
父亲坐在一边,冷冷的讥讽,“才有多痛点呢,我这只脚都断了,我的痛不比你的厉害?”
父亲前几年在井下,被矿车挤断了腿,住了一年多的医院,在那段时间里,父亲的脾气变得很怪。出了医院后,父亲的腿跛了,只能干点轻松的工作,在矿上成了“游手好闲”的人。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很拮据,母亲就出去到打石场、洗煤厂、石灰窑等地打短工。
母亲的工友把母亲扶回家就走了,父亲说他脚是跛的,背不动母亲,从家到医院只有我来背了。十五岁的嫩肩托着母亲的重量,我的双脚如轮子转动,转成一种飘浮的柔软。在几次差点软下脚去时,我都咬牙坚持不倒,停一停,歇口气,继续走。
边走边想,在今后的路上,将有比母亲的身体更重的东西压上肩,无论多沉重,都要直直的站立,绝不能软下去,更不能跪下地、或趴到地上去。
母亲躺上病床以后,我把红红的通知书递给母亲看,却把白色的写了数字的纸藏了起来。那上面的数字,是我所知道钱以来,面对的最大的数字。我和父亲出了门,把那张纸递给父亲,父亲脸上的肌肉扯了扯,没讲话。走出很远了,父亲才淡淡的说,“可能要借借了。借也只有你去,拿个通知书,而且是孩子,要好借些。”我们家经济状况一直紧张,借钱,很多人都不敢借,为什么?还不是怕久拖还不了。
我出门去借也并不顺利,我找的与我们家熟识的人,家庭情况跟我们家也差不了多少,能借的只是一个很少的数。奔来波去,几天了,数数借的钱和家里余钱的总数,还有一个缺口。
“现在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干脆找个地方干点活,挣点钱,这缺口就小多了,然后再加上你走那个月我的工资基本上就够了。”
“可去那里打工呢?现在矿上工资发不出,很多家属都想找活干都找不到,我怎么找?”
“在矿上找不到,就去附近农村找。听你李叔说,离这不远有个村子,村里有个叫林强的人开了个采石场,他想找个帮手。”
“他会要我?”
“他那个采石场就象个家庭作坊,在他的承包地里开采,开出来就卖给矿上。你李叔管石方的检查验收,他正巴不得你李叔介绍人去,既解了他用人的问题,又解了他巴结李叔的问题。”
我找到林强,他正蹲在他家的门边,小小的身子却在西去的太阳帮助下,铺起长长的影子,我也蹲下去,影子把我的前额到下巴都占领了。我看着他,他正在检查一堆灰灰的搓成圆棍样的炸药。
“就这么几根屎橛子一样的东西,就要五十块钱,真他妈的黑呀!”
那个身影低低地嘀咕着。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林强,叫老板呢,还是林哥。林强在我迟疑之际抬起脸,眼睛小小地躲在他的脸上,里面射出的是狡黠的光。眼睛就被脸和眼光遮住了,让人要费力去寻找似的,脸的老成在稚气的皮肤陪伴下有些不协调。“叫我林哥就行。”我的紧张一下子得到了舒解,淡淡的红潮布满了我的脸颊。
“你的情况李叔都跟我说了,从现在到你开学,你跟我干两个月,每个月六十块钱,少来一天减两块,怎样?”
林强说的数我己在李叔处听说过,林强再说一遍,不过是双方当面敲定。这个数字跟妈妈在石灰窑干一个月的数差不多,我就是冲着那个小小的数子来的。
二
林强也不大,刚二十出头。他的采石场就在他家的地边,沿路看过去,有好几家这样的采石场。在采石场的外面,是一组从矿上运煤出去的小轨道,小轨道上经常有叮铃叮铃的矿车开过。李叔一般上午十点过来,看过几家开出来的石头后,就安排矿车来装。
在这个采石场上就我们两个人,其它的采石场上的人也不多,顶多三个人,都是兄弟帮、或父子帮。没去几天,我就看出点端倪,李叔对采石场有重要作用。他一去,大家都把活丢下,围在他身边,递烟,套近乎。李叔一到那里,白白的长棍样的烟一边耳边夹一根,手上还捏一根,别人再递给他,他也不要了,别人给他点火,他也不点,后来才听说,他是不抽烟的,他把烟拿回去,装好,给他下井的舅子抽。跟李叔关系好的,当天采下的石头都收,跟李叔关系不好的就只收一部分或以质量不好的理由,全都不收。
林强确实有超出别人的关系,再加上李叔介绍了个人去,林强采的石头都通通拉走了。这对林强是好事,对我是苦事,既然采多少,李叔收多少,林强就开足马力干。旁边的有些采石场就没那么忙,出工晚,干不多久就坐下吹牛,反正采出来堆在那里还不是堆在那里,装不进李叔安排的矿车,它就只是硬梆梆的石头,不是暖和爱人的钞票。
不过他们也不着急,有农村人的忍耐和认命。石头采多了没人要,就松松散散干,多吃口烟,多吹会闲天,或者干脆把那块采石的地上还种有的玉米松松土,除除草。再不,看几天石头还是石头,就趁天黑,抓只老母鸡或者提块腊肉去李叔家,第二天就有矿车停在他家采石场门口了。
在简陋的采石场上,并没有什么工具,隔几天喊个人来在石崖上打几个眼。然后就在眼上填上从黑市买来的炸药,炸上几炮。炸落下来的石头大小不一,要符合李叔要的规格,还得把大的石头用大锤打小,一般每块有四、五十斤就行了。然后整整齐齐码放在路边,等李叔安排的矿车过来,我们再把石头装上车。
每天林强抡锤,我就把那些石头搬来抱去,或者拿筐把采石场炸下的泥弄到边上去。几十斤的石头,尖尖的棱角,割得我手上到处都是伤口。以前在学校,手握的都是笔,那里抱过石头。
每次看矿车走远,林强转过背到采石场里继续干,我久久的站在那里,两只眼睛仿佛都被夹在石头中间,被拉到黑暗的井下,拌上混凝土土,永久地埋在下面。
每天大部分时间里,我的手都被石头占据了。那些尖棱多角的石头,抱在怀里,一块又一块,走过去又走过来,百次千次的重复。父亲以前下井穿过的劳动布工作服被磨出了洞,母亲又拿了块同样的布补上。
每一块石头,每一次移动脚步,都给我身上娇嫩的肌肉留下记忆。疲累仿佛有千万只手在拉我扯我,收工回到家,躺在床上,身上的肉如虫在咬,每一块肉都要脱开骨头,分散开来,各奔各的方向,离开这文火烧烤着的身体。
疲累对于我的身体,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几天以后,那种浑身疼痛的感觉渐渐淡化了,饥饿成了难以逾越的高山。
母亲从医院出来,躺在床上,总觉得口味寡淡。她拖着一只伤腿到灶前,舀一碗米,掺一锅水,把饭熬得烂烂的,稀稀的。妈妈喝一碗就没了食欲,推碗上床。
父亲归家的时候很少,下了班不是打牌就是下棋,晚了就跟人打平伙。偶尔回到家,一杯酒放桌前,从小卖店买半包花生米,慢慢嚼。酒喝完,稀饭是不沾的,煮碗面条吃,照他的话说,就好口酒,好碗面条。这口酒就是家里的买完粮本上的粮后剩的钱,进肚了;这碗面,是家里粮食的一半,进肚了。喝了酒,总是要发发牢骚,说说李叔,如何吃香的喝辣的,说当官的,如何黑暗。有几次,我都看见父亲在上班的时候,如何跟在李叔后面,说着笑话,跟在当官的后面,陪着小心。
我喝两碗稀饭,还想吃,但肚子滚圆了。走出去,刚到采石场上,拉一泡尿,肚子平了。抱到第三块石头,第二泡尿下来,肚子就扁了,雷声起了。
我记得以前有人对我说过,“吃鹅卵石或者钢珠,怎么都变不成稀屎,肚子就一直胀鼓鼓的,就不会饿。”现在我的脚边、手上到处都是石头,那些尖尖的棱角割着我身上的肉,肚子被雷锤击得火辣辣的。我正躲在一块玉米地边的一块光滑的大石下,石头对着一条小路,我看着小路的两端,看见有人走过,就喊“放炮了,放炮了。”过路的人就藏在路边,等炮响过了才走。
林强点燃了炸药,往他藏身的石头下面跑去,身影在我眼睛里迅捷地一闪,不见了。
炸药的引线在不远处燃,四周都屏住了呼吸,静静悄悄的,连蚂蚁也没走动了。静寂放大了肚里的声音,林强嘣嘣跑动后留下的余音,一直波涌到我的肚皮里,两股声汇成一股,形成一根粗粗的棍子,在肚里搅动。
三
燃烧的导火线不断地把火推到前方,粗粗的棍子在肚里搅得难受,青青的玉米叶垂拂下来,遮在眼前。凉爽清香的玉米棒子穿过裹紧的外皮透出来,丝丝淡淡的递进鼻里。肚子支使手,快捷迅猛地直伸上去,拉下头顶边的一个绿色玉米棒子。玉米棒子受到猝然一击,如一只青蛙扑通一下跳起来,不是跳进了池塘,而是跳进了我干瘦有力的手中。我胡乱地撕开青色的外衣,就如一个眼中喷火的强奸犯,动作迷狂混乱。牙疯狂地压上去,棒子上留下一排渗满乳白色汁液的牙印。头脑想发挥作用,把牙齿的动作稳定下来,一迭声地命令,“立正、立正。”但牙齿只接受肚子的命令,根本不听头脑的话。
牙齿杂乱地,奔跑着,头上轰轰隆隆的传来炸药的爆炸声,嘴里满是乳白色的汁液。肚子接收到它需要的礼物时,整个身体都松弛下来,身上的力气都散开了,身体舒展地铺展开。我头靠到石头上,方便牙齿快捷地工作,脚伸了出去。
肚里的嗝爬了上来,表达它的满意。嗝的气味是清清香香的,从头上来的碎石跌下地来,洒到我的脚上,裤子没烂,但在腿上排了几个红点。我没有心思去顾及这些,我所有的心思都花到了那根青色的棒子上,牙齿咔嗒咔嗒地数着棒子上的“毛孔”。很快“毛孔”都数进了肚里,光光的棒子成了癞皮蛇,样子很难看。路边有人走过了,其它几个采石场的人也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缓缓的讲着话。
我有些醉了,眼睛迷离起来。这时另一根棒子递到我手里,我机械地开动牙齿,咔嗒咔嗒一往无前。牙齿开动起来就觉得不对,牙齿被磕得崩崩地脆响。我圆睁了两眼一看,手中哪里是玉米棒子,而是一块长长的石头。
我狠命地吐了几口咬在口中的碎石,然后拿眼去看站在前面的林强。林强一副很恼怒的样子,他蹲下身,捡起地上那截啃丢的棒子,棒子上的牙印走得很乱,错落地留有些玉米粒和没啃掉的玉米皮。
“这种没长饱满的玉米都啃!一啃一包水,你太不珍重农村人的劳动了,你们城里真是太坏了。”
“不是,我……我……”我想辩解,可话却说不出口来。
“辩解什么?难道我说错了,一个城里娃娃,除了能读几本书,识几个字,其它还能干什么?我看你搬石头那轻飘飘的样,就知道你是个熊货,还不是靠着李叔的关系……”
我脸涨得通红,又找不出词来反驳。在矿区周围的农民,对矿区的工人,天生有因羡慕而生的看不顺。进九十年代后,这周边的农村人由于经济搞活,做点小生意或打点工,经济条件都好起来。而矿上却陷入久拖不决的债务纠纷中,工资不但不涨,而是按80%、75%、50%的坡度下滑。而一个矿区的孩子,走到林强的采石场上来打工,挣他的微薄工资了,林强的自信心浮夸地增大了。
看不顺眼就看不顺眼吧,现在低头在林强的屋檐下,他说什么由他说去好了。我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往采石场走,甜甜的清香塞在两腮之间,满满地聚拢了不少散失的力气。
石头炸滚到采石场下,整个采石场上一片狼籍的样子。“快干,一会李叔安排的矿车就来了,我们要多准备点,昨天去了他家一趟,说今天给我们四个车。”
刚炸下的石头很多,我们先把一部分基本符合条件的石头抱出来,然后再弄出一些稍做修整的石头。为了抢时间,我们干得很快。放炮的第一天,出石最多,而今天李叔说井下缺石头,安排的矿车很多,其它几个采石场都抓紧了进度,这么好的机会林强更不会放过。
四
干到吃饭点,矿车来了。林强说装完车再回家吃饭,我也没办法,干吧。越干到后面越不行,虽然刚生啃了一个玉米,又是一个还没长饱满的玉米。稀稀的汁一样的玉米,我去草丛里拉了一次屎就空了。
工作速度上不来,林强也知道原因。其它几个采石场的速度比我们快多了,矿车停在路上,司机不停地催,“快一点,快一点,井下等用。快不了就把给你们的矿车让给别的采石场。”林强着急,也没办法。
越急动作越缓慢,司机越催得凶,“快点,我拉到井下,好早点下班。中班忘了带饭,肚子都饿了。”
“你去我家的地里,扳几个包谷,就在路边烧起吃。”林强从司机话中的“饿”字上找到了原因。
共 1281 字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吃相凶猛,一个“吃”字,道尽了生活的艰难!作者的这一篇小说,咋一看去,平淡中颇有些质朴,整体的语言,除了偶然的对于生活环境的描述,诸如矿工的生存环境,周边的玉米林等,又或者是在心理活动的描述上,刻画得非常精彩之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简简单单的短句子,纯粹的交代着事情的发展,但是,就文章本身,所渲染出来的对于底层生活的经历,以及“我”这个当事人,所亲眼看到的,感受到的,却是非常的深刻!文章的一开篇,就是一场意外,而到了“我”为了学费,而去尝试着辛苦劳作赚钱的时候,意外更是接踵而至,这其中所牵连出来的一系列的人物,诸如林强、玉凤、村长,等等,在人物个性上,都是非常的鲜明的,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推演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群体,都有着大致的情况存在。这就使得这篇小说的意义,变得更加的广泛起来,有着更为强烈的可读性。而小说的行文中,时而的会出现,“我”在吃这一方面的具体描述,乃至于是到了收尾部分,依然在不断的提点着,宁愿做一个饱死鬼,也不要做一个饿死鬼,这种最为朴质的观念,相比起林强因为权势之类的压力,违心的去接受“丑陋的”玉凤的婚姻而言,何尝不是更大的悲哀和讽刺?倾情推荐。——履泽【江山部·精品推荐 】
1楼文友: 07:21:05 问好作者,很不错的作品,欣赏了。
欢迎赐稿江南烟雨社团,祝福夏日愉快。
期待更多精彩。
2楼文友: 20:58:12 非常感谢履泽老师的精彩点评。这个故事,是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难忘经历。生活的艰难,反映出来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吃 。 爱思考,爱读书,爱文学。
楼文友: 1 :50: 9 每次看特快专列的小说都很振撼。平常人物平凡事,却总能深深打动人心。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平常生活中,人物一个个立起来了,那样的真实,那样鲜活。学习了!
小孩不爱吃饭是怎么回事云香精价格多少钱一瓶张掖白癜风治疗费用中山治疗白癜风好的医院- 上一篇:感事咏怀
- 下一篇:[p]供享是一款最受时下年轻人喜爱的手机直播软件

-
清明时节鱼塘杀虫消毒管理位置
西餐2022年06月13日

-
使用毛巾给短毛猫做清洁工作位置
西餐2022年06月13日

-
使小斗牛犬流眼泪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位置
西餐2022年06月13日

-
你留意到可卡犬为何会体臭吗位置
西餐2022年06月13日

-
你是适合饲养比熊犬的那一类人群吗位置
西餐2022年06月13日